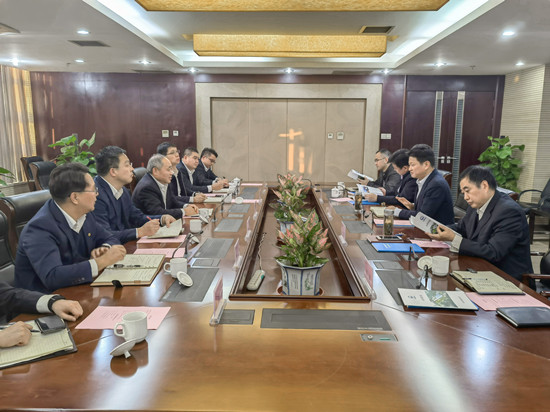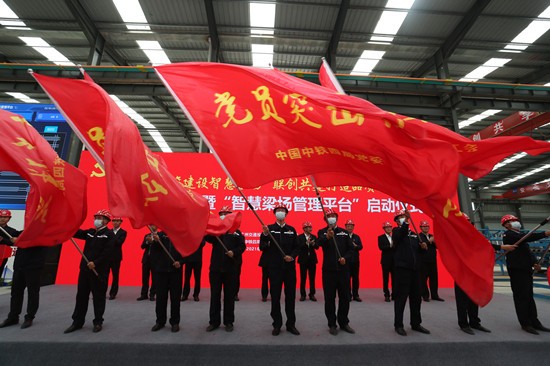第一财经日报:坦赞铁路采访侧记 赴非投资ABC
2012年08月31日
第一财经日报作者:陈晓晨
中非关系到底好不好?
很多人一提到非洲,就是《动物世界》里的草原、狮子景象,要么就是饥荒、瘦弱的面孔甚至想象中的“食人族”场面。而提到中非关系,往往还停留在“阶级兄弟”的时代。
现实的非洲和中非关系,远比脸谱化的形象复杂。
好的一面仍然存在。有些老非洲人,确实还记得中国人对他们的“无私援助”。随着中国国力不断增强,很多年轻的非洲人也知道中国“现在有钱了”,生产了很多产品。当然,这些印象中也夹杂着非洲式的夸张,如“中国比美国还富”。不少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是勤奋工作,传说中国人居然晚上还工作,这太不可思议了。
当然,也有很多不好的印象。比如:“中国的产品都是残次品”——中国的各种山寨产品充斥非洲市场,而缺乏“一分钱一分货”意识的当地人又确实喜欢便宜货。又如“中国企业虐待劳工”——不少赴非中资企业缺乏对当地法律和文化的认识,把国内的加班、多劳多得等习惯带到非洲,对最低工资、劳动保护等缺乏概念,引发了非议。这两点极大地消耗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在非洲建立的良好形象。
“走出去”战略已经实施10年左右。现在,到了升级换代的时候了。需要系统地提升“走出去”的质量。这样,才能避免对中非关系的进一步消耗。
适应非洲水土
在非洲,流传着很多关于中国人的谣言。其中最有传播力的谣言之一,就是“中国在非洲使用囚犯当劳工”。笔者在非洲采访时,也被问到过这个问题。
这条谣言看似荒诞不经,但并非没有根基:在非洲的中国人确实在衣着上不注意,与当地人交往少,居住环境差,工作强度大,而且男女比例严重失调,与非洲人眼中养尊处优的“白人”形象相去甚远,而确实有点像“囚犯”了。
中国人工作勤恳,确实让一些非洲人以为只有囚犯才如此辛苦。比如,中国人对“加班”习以为常。但在非洲,休息可是上帝赐予的权利。“加班”是贬义词,有时等同于“压榨”乃至“虐待”。笔者对一个非洲人解释,说笔者经常工作到夜里一两点。听者瞪大了眼珠张大了嘴,半晌才冒出一句:“你……是囚犯吗?”
这里还有个深层问题。根据非洲很多国家的劳动法,企业必须雇用较高比例的当地员工。而中国企业和项目大多还是习惯带去中国劳工,一是效率高,二是服从管理。这是一个矛盾。
对“中国囚犯”谣言的破解,在于“走出去”,不要把自己封闭在高墙大院之内。与当地人交往,才能适应非洲水土。
“潜规划”无所不在
在不少非洲国家,腐败是从上到下、“深入人心”的。
索贿往往从入境就开始了。边检员经常难以对付,时常要付出比正规费用多得多的“潜规则”。此后,索贿将一直伴随你,直到你离境,还要被盘剥一次。
腐败给投资者带来很大困扰。大到办理营业执照,小到街上检查身份;上至国家官员,下至基层警察,“潜规则”无所不在。中国投资者往往陷入两难:不行贿,就要承受旷日持久的等待,乃至各种找茬;出了钱,又可能被眼尖的西方媒体或受西方影响的本地媒体曝光。左右不是人。
要钱的理由五花八门。常见的有“我家房子着了火”,“我家亲戚得了病”,“我家孩子上了学”等。最常见的理由是“我还没吃饭呢”,一只手指肚子,另一只手就伸了过来。
有一次,警察当街拦下了笔者租的车——笔者已经对此见怪不怪了。男警察很是“绅士”,指着旁边的女警说,“她还没吃早饭呢”。笔者当时可能是疟疾上身,脾气很坏,就是不给钱。警察急了,指着笔者的车说:“别的车都是白色,你的车为什么是红色?颜色不对,罚款!”
在不少非洲国家,无论是市场问题、行政问题、司法问题,乃至政治问题,到最后都简化成一个字:钱。这成了制约非洲发展进步的障碍,也是赴非中国企业面临的困难。
伸出的手
在非洲,如果迎面一个陌生人走来,问你:“可以把你的手机给我吗?”不要害怕,他不是抢劫犯,也不是乞丐,只是一个习惯索要的普通非洲人。
长期以来,非洲得到了大量外援,大部分来自西方。这多少是在道义上“补偿”西方对非洲的殖民血债。然而,道义归道义。不争的事实是,大量外援使一些非洲人产生了“等、靠、要”的习惯。
索要,在这里是一种习惯。即使完全陌生,也会朝你要这要那,开口绝不会脸红。更不用提在大街上游荡的人,一只手指着肚子、另一只手伸出来向你要钱。他们的逻辑似乎是:“我饿肚子是你的错,所以你要给我钱。”
在援建坦赞铁路过程中,中国人“把工地当学校”,为非洲培养了一批人才,试图加强当地独立自主意识。其中就包括笔者采访的马奎塔、哈吉、诺亚、里姆比里等人。
然而,这种思路虽然培养了一些个体,但并未改变依赖外援的思维习惯。今天,当“市场经济的新中国”再次来到非洲大陆的时候,不少当地人想的仍然是“你把钱给我”,而不是“我们一起用它赚更多钱”。结果,当他们看到中国人大把大把地赚钱的时候,心理就开始不平衡了。矛盾也由此产生。
基础设施与上层建筑
在坦赞铁路沿线采访时,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经常被糟糕的基础设施困扰。土路仍然常见,甚至在首都的使馆区居然也有不少土路。到了雨季,有些土路就会变成泥淖,无法行车,有几次耽误了行程。这就是为什么在非洲做事,必须要留有充足的时间。
出行的困难也就罢了,大不了多留一两天。对本报记者来说,最不能忍的是洗澡问题。
在非洲腹地,澡水是稀缺资源。当地人很多都在水井旁直接洗澡,男男女女都有。笔者脸皮不够厚,还做不到这一点。笔者靠的是“DIY澡水”,即从井里打水,烧开,然后提着一桶水自己洗。出门之前,要预约好澡水,否则就要在近40度的大热天出着汗黏糊糊地睡觉了。难受还不是问题,主要是招惹蚊子,引疟疾上身。
然而,在如此之差的基础设施上,却又盖着非常超前的上层建筑:极严苛的劳动法、强大的工会、有些随意的罢工权和西方式民主制度。雇主如果想给员工降薪或解雇,极为麻烦,哪怕员工偷窃公司财物,也要经过一犯教育、二犯警告、再犯开除的程序。成规模的企业必须成立工会。工人对薪资不满,首先想到的不是跳槽,而是停工乃至罢工。而劳动制度的背后,是西方式民主制度的支撑。
过于严苛的劳动制度,降低了对外资的吸引力,阻碍了投资与经济发展,也无法提供更多就业。实际上,这保护了工作能力不强的员工,损害了年轻的求职大军。笔者看到,大街上到处都是闲逛闲聊无事可做的年轻人。到头来,埋单者还是落在劳工头上。
赴非投资的中资企业,应首先做好当地劳工法和政治形势的功课。要熟悉最低工资、工会、罢工和政治性事件等。不能按国内的节奏做事,不要轻易安排加班,要一天的事拆成两天做。
疟疾
疟疾与艾滋病并列为非洲人的主要杀手。2010年,据估计有少则数十万、多则数百万非洲人死于疟疾。
笔者在旅行中也疑似中招:一天凌晨,笔者心悸惊醒,一试体温,40.5度。笔者见势不妙,立刻服下抗疟药青蒿素。两小时后,高烧退去,满身大汗,浑身无力。此后,发烧和出汗还反复发作了几次,周身乏力,思维停滞。
几十年来,中国向非洲很多国家都派出了医疗队。笔者在赞比亚期间,援赞医疗队为笔者进行了诊治。这些医疗队为中国在非洲的良好形象起了很大作用。
非洲人的幸福
在非洲,本报记者与当地人打成一片,和他们同吃、同喝、同玩甚至同住过。在与他们的接触中,在他们的汗味熏染下,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。
非洲人天生能歌善舞。下了班,就去跳舞。不需要认识,陌生人聚在一起就能舞起来。不需要排练,就能跳出舞台效果。每当笔者置身其中,就立即被非洲人的热情同化了。经常有当地人夸赞笔者,是舞跳得最好的中国人。当然,笔者明白,这是因为不少中国人并不乐意融入当地。
在与当地人玩乐之余,笔者也时常被一个问题困扰:为什么他们挣得比我们少十倍,生活条件如此之差,但却似乎活得比我们还开心?
非洲人的性格是乐天的。他们享受生活,不拘泥生活中的烦心事。只要有音乐,就能忘却所有烦恼。只要领了工资,就出去买酒或其他享受,不醉不归,或干脆不归。一个晚上,就能花掉半个月工资。拿了钱,人就没影了;钱花完了,再回去工作。他们很少有“储蓄”的观念,而更像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”,不想明天。
一方面,本报记者着实羡慕他们,觉得中国人应当学习非洲文明中的乐天心态。另一方面,这也确实制约着非洲经济的积累——他们中的很多人根本没有“积累”这个概念。
- 相关阅读